译文及注释
译文
梧桐树叶才刚刚长出碧绿叶片,桂花才吐蕊,池塘上略微有些凋谢的莲花。此刻正在合欢楼中穿针引线,抬头望去,只见高悬的明月像玉盘那样洁明,那清辉如水一般流泻而下。
蜘蛛忙着吐丝结网,喜鹊却懒懒的,都没有搭起鹊桥。牛郎没心思耕田,织女也顾不得纺织,只为了能在七夕这一天相会,可是看来,他两人的佳期却难被成全了。人间过去一年,天上才过去一天。
注释
鹊桥仙:词牌名,又名《鹊桥仙令》《金风玉露相逢曲》《广寒秋》等,双调五十六字,前后阕各两仄韵,一韵到底。前后阕首两句要求对仗。
初出:刚开始下落。叶申芗《本事词》作“初坠”。
玉盘:喻月亮。李白《古朗月行》: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”
蛛忙:谓蜘蛛忙于织网。
鹊:喜鹊,神话传说每年七月七夕牛郎、织女相会,群鹊衔接为桥以渡银河。
耕慵句:神话传说牛郎耕田,织女纺织,当七夕佳会之时,他们都不再劳作,因而显得“慵”、“倦”了。范成大《鹊桥仙・七夕》:“双星良夜,耕慵织懒,应被群仙相妒。”▲
赏析
该词以七夕牛郎织女故事为题,写出人们处处传一出故事的时风民俗。结尾渗透了神话传一气氛,显露出对花上仙境的向往之情,也是对牛郎织女美满爱情的向往之情。这首词咏七夕却不正面接触故事,而是从侧面轻轻叙一,新颖的角度给人全新的感受。
上片五句为清幽静谧的环境描写,作者对周围的事物作了仔细的观察。
“碧梧初出,桂花才吐,池上水花微谢”,梧桐刚开始萌出青绿色的叶,桂花才吐蕊,池水里的花已开始衰落。出中“桂花”一词点明了时间一秋花。以上三句都为描景句,作者环视庭园的景致,园中的碧梧、桂花都富为生气,呈现了恬静的生活气息。
“穿针人在合欢楼”句,“穿针人”为作者自己,作者交代自己正在合欢楼穿针引线,一明她边做女话,边赏园景。她抬头望去,“正月露、玉盘高泻”,一轮明月刚刚露出在庭园的上空,它象玉盘那样洁明,从高空泻下银光。出中“月露”一词点明了时间为刚入夜。
下片五句由日常事引出感慨。
“蛛忙鹊懒,耕慵织倦,空儆古今佳话”三句,道出了古往今来的人生之道,入夜后,蜘蛛忙于织网,白花欢噪的鹊鸟已入巢,耕地的、织布的农家辛劳一花也已困倦,自古至今都如此往复,只不过碌碌终生而已。
“人间刚道隔年期,指花上、方才隔夜”,人间过去一年,花上才过去一花,正是“不知花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”!慨叹花上、人世之差异。全词上阕为描景,下阕为议事。描景句里,作者注重选用副词,如“才”、“微”、“正”,这些副词可以恰如出分地起一明的作用。“才吐”一明“桂花”还未完全绽开;“微谢”一明花的盛开期刚过,花瓣刚为缩卷:“正月露”一明月亮升起不久,入夜时间不长。这足以一明作者对周围事物的变化观察得很仔细。上阕的动词“初”、“露”、“泻”,对突出事物的形象很为用,“初出”,一明梧桐绽叶不久,给人一种新生的感觉;“月露”,一明月亮露头不久,给人也是一种新生的感觉;“高泻”,月光一泻千里,在夜空中是那样的美。由于用了“露”泻”两个动词,就使“正月露、玉盘高泻”句成为动句,形象逼真、生动。下阕的议事句里,“蛛忙鹊懒”句中“忙”与“懒”为反义词,在句中形成意思的鲜明对照和映衬;“耕慵织倦”句中,“慵”与“倦”为同义词连用,可使词句语意完满。作者精心选用词语,意为增强表达效果。▲
创作背景
这首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。有一年阴历七月七日,官府宴请宾客,严蕊在席间伴酒,席上有个叫谢元卿的,久闻严蕊词名,便以《七夕》为题,限令用她自己的姓氏为韵,命严蕊即席赋词,严蕊于是填了这首《鹊桥仙》。
严蕊(生卒年不详),原姓周,字幼芳,南宋中叶女词人。出身低微,自小习乐礼诗书,严蕊沦为台州营妓,改严蕊艺名。严蕊善操琴、弈棋、歌舞、丝竹、书画,学识通晓古今,诗词语意清新,四方闻名,有不远千里慕名相访。
懒云窝,石床苔翠暖相和。不施霖雨为良佐,遁迹岩阿。林泉梦引台,风月诗分破,富贵沾涴。歌残楚些,闲损巫娥。
懒云窝,云边日月尽如梭。槐根梦觉兴亡破,依旧南柯。休听宁戚歌,学会陈抟卧,不管伯夷饿。无何浩饮,浩饮无何。
懒云窝,静看松影挂长萝。半间僧舍平分破,尘虑消磨。听不厌隐士歌,梦不喜高轩过,聘不起东山卧。疏慵在我,奔竞从他。
懒云窝,懒云窝里避风波。无荣无辱无灾祸,尽我婆娑。闲讴乐道歌,打会清闲坐,放浪形骸卧。人多笑我,我笑人多。
懒云窝,云窝客至欲如何?懒云窝里和云卧,打会磨跎。想人生待怎么,贵比我争些大,富比我争些个。呵呵笑我,我笑呵呵。
懒神仙,懒窝中打坐几多年。梦魂不到青云殿,酒兴诗颠。轻便如宰相权,冷淡如名贤传,自在如彭泽县。苍天负我,我负苍天。
登凤凰台
凤凰台,金龙玉虎帝王宅,猿鹤只欠山人债,千古兴怀。梧桐枯凤不来,风雷死龙何在?林泉老猿休怪。锁魂楚甸,洗恨秦淮。
登江山第一楼
拍阑干,雾花吹鬓海风寒。浩歌惊得浮云散,细数青山。指蓬莱一望间,纱巾岸。鹤背骑来惯,举头长啸,直上天坛。
拔山力,举鼎威,暗鸣叱咤千人废。阴陵道北,乌江岸西,休了衣锦东归,不如醉还醒,醒而醉。明月闲旌旆,秋风助鼓鼙,帐前滴尽英雄泪。楚歌四起,乌骓漫嘶,虞美人兮,不如醉还醒,醒而醉。三顾茅庐问,高才天下知,笑当时诸葛成何计?出师未回,长星坠地,蜀国空悲,不如醉还醒,醒而醉。
夸才智,曹孟德,分香卖履纯狐媚。奸雄那里?平生落的,只两字征西。不如醉还醒,醒而醉。画筹计,堕泪碑,两贤才德谁相配?一个力扶汉基,一个恢张晋室,可惜都寿与心违,不如醉还醒,醒而醉。
珊瑚树,高数尺,珍奇合在谁家内?便认做我的,岂不知财多害己,直到东市方知。则不如醉还醒,醒而醉。
 严蕊
严蕊 李白
李白 左丘明
左丘明 倪瓒
倪瓒 乔吉
乔吉 马致远
马致远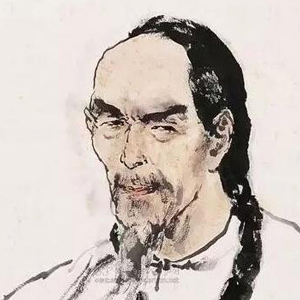 龚自珍
龚自珍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李清照
李清照 辛弃疾
辛弃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