乙卯秋月十九日登泰山太平顶
穷秋老雨四十日,坤轴欲烂阴霾缠。我来方作泰山游,玉虹一夜收云烟。
山灵奕奕生喜色,突兀撑裂青罗天。轻裾飘飘过黄岘,乘兴直到三峰前。
霜馀灌木出秋色,万叠红锦幪椒巅。泓澄寒溜浸太古,翠壁细泻珠玑圆。
当时秦汉极侈丽,未必如此皆天然。天门中断两屹立,箭筈一磴蛇蜿蜒。
凌层绝顶肆崇峻,伫立矫首望八埏。长天沈沈入西极,九州却在东海边。
冲风惨淡万里来,海窟劲刮鲲鲸涎。须臾白云生岳麓,脚底泱莽无山川。
秦坛周观觉浮动,满地覆冒兜罗绵。忽疑山移入海中,白浪四汹虚涛掀。
山阴瑰诡光怪出,赤气翠晕相钩连。下从谷底上碧落,宝塔万级高蟠旋。
遂登日观叱日驭,六龙倒著珊瑚鞭。玉鳞剥落金甲拆,九芒迸绮生血鲜。
三山摇荡海水沸,蓬壶缥缈来飞仙。为言此色与此界,君自固有非尘缘。
恍然记悟复无语,把手一笑三千年。
(1223—1275)元泽州陵川人,字伯常。郝天挺孙。金亡,徙顺天,馆于守帅张柔、贾辅家,博览群书。应世祖忽必烈召入王府,条上经国安民之道数十事。及世祖即位,为翰林侍读学士。中统元年,使宋议和,被贾似道扣留,居真州十六年方归。旋卒,谥文忠。为学务有用。及被留,撰《续后汉书》、《易春秋外传》、《太极演》等书,另有《陵川文集》。
秦将王翦破赵,虏赵王,尽收其地,进兵北略地,至燕南界。
太子丹恐惧,乃请荆卿曰:“秦兵旦暮渡易水,则虽欲长侍足下,岂可得哉?”荆卿曰:“微太子言,臣愿得谒之。今行而无信,则秦未可亲也。夫今樊将军,秦王购之金千斤,邑万家。诚能得樊将军首,与燕督亢之地图,献秦王,秦王必说见臣,臣乃得有以报太子。”太子曰:“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,丹不忍以己之私,而伤长者之意,愿足下更虑之!”
荆轲知太子不忍,乃遂私见樊於期,曰:“秦之遇将军,可谓深矣。父母宗族,皆为戮没。今闻购樊将军之首,金千斤,邑万家,将奈何?”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:“吾每念,常痛于骨髓,顾计不知所出耳!”轲曰:“今有一言,可以解燕国之患,而报将军之仇者,何如?”於期乃前曰:“为之奈何?”荆轲曰:“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,秦王必喜而善见臣。臣左手把其袖,而右手揕其胸,然则将军之仇报,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。将军岂有意乎?”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:“此臣之日夜切齿拊心也,乃今得闻教!”遂自刎。
太子闻之,驰往,伏尸而哭,极哀。既已,不可奈何,乃遂盛樊於期之首,函封之。
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,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,取之百金,使工以药 淬之。以试人,血濡缕,人无不立死者。乃为装遣荆轲。
燕国有勇士秦武阳,年十二,杀人,人不敢与忤视。乃令秦武阳为副。(秦武阳 一作:秦舞阳)
荆轲有所待,欲与俱,其人居远未来,而为留待。
顷之未发,太子迟之。疑其有改悔,乃复请之曰:“日以尽矣,荆卿岂无意哉?丹请先遣秦武阳!”荆轲怒, 叱太子曰:“今日往而不反者,竖子也!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,仆所以留者,待吾客与俱。今太子迟之,请辞决矣!”遂发。
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,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上,既祖,取道。高渐离击筑,荆轲和而歌,为变徵之声,士皆垂泪涕泣。又前而为歌曰: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!”复为慷慨羽声,士皆瞋目,发尽上指冠。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,终已不顾。
既至秦,持千金之资币物,厚遗wèi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。
嘉为先言于秦王曰:“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,不敢兴兵以拒大王,愿举国为内臣。比诸侯之列,给贡职如郡县,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。恐惧不敢自陈,谨斩樊於期头,及献燕之督亢之地图,函封,燕王拜送于庭,使使以闻大王。唯大王命之。”
秦王闻之,大喜。乃朝服,设九宾,见燕使者咸阳宫。
荆轲奉樊於期头函,而秦武阳奉地图匣,以次进。至陛下,秦武阳色变振恐,群臣怪之,荆轲顾笑武阳,前为谢曰:“北蛮夷之鄙人,未尝见天子,故振慑,愿大王少假借之,使毕使于前。”秦王谓轲曰:“起,取武阳所持图!”
轲既取图奉之, 发图,图穷而匕首见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,而右手持匕首揕之。未至身,秦王惊,自引而起,绝袖。拔剑,剑长,操其室。时恐急,剑坚,故不可立拔。
荆轲逐秦王,秦王还柱而走。群臣惊愕,卒起不意,尽失其度。而秦法,群臣侍殿上者,不得持尺兵;诸郎中执兵,皆陈殿下,非有诏不得上。方急时,不及召下兵,以故荆轲逐秦王,而卒惶急无以击轲,而乃以手共搏之。
是时,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。秦王方还柱走,卒惶急不知所为。左右乃曰:“王负剑!王负剑!”遂拔以击荆轲,断其左股。荆轲废,乃引其匕首提秦王,不中,中柱。秦王复击轲,被八创。
轲自知事不就,倚柱而笑,箕踞以骂曰:“事所以不成者,乃欲以生劫之,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”
左右既前,斩荆轲。秦王目眩良久。
冻雪才消腊梅谢,却早击碎泥牛应节,柳眼吐些些。时序相催,斗把鳌山结。
【喜迁莺】畅豪奢,听鼓吹喧天那欢悦。好教我心如刀切,泪珠儿揾不迭,哭的似痴呆。自从别后,这满腹相思何处说。流痛血,瑶琴怎续,玉簪难接。
【出队子】想当初时节,那浓欢怎弃舍。新愁装满太平车,旧恨常堆几万叠,若负德辜恩天地折。
【神仗儿】这些时情诗倦写,和音书断绝。斜月笼明,残灯半灭。恨檐马玎当,怨塞鸿凄切。猛然间想起多娇,那愁闷,怎拦截。
【挂金索】业缘心肠,那烦恼何时彻。对景伤情,怎捱如年夜。灯火阑珊,似万朵金莲谢。车马□阗,赛一火鸳鸯社。
【随尾】见他人两口儿家携着手看灯夜,教俺怎生不感叹伤嗟。尚想俺去年的那人何处也。
怀离
行色匆匆易伤感,陡恁般香消玉减,无暇理金簪。云鬓髧鬖,比是情凄惨。避不得这羞惭,准备遮藏手半掩。
【喜迁莺】想才郎丰鉴,貌堂堂阔论高谈。那堪。并不愚滥,一见了春愁独自搅,常好是忒大胆。怕不你心心儿里待贪,又则怕意意儿里相搀。
【出队子】想人生时暂,在绣房中把岁月耽。描不成映花梢孔雀翠相搀,剪不出扑柳絮胡蝶粉乱糁,刺不就啄谷穗鹌鹑嘴细嗛。
【刮地风】则被这几对儿家毛团迤逗俺,马儿送的人地北天地。待私奔至死心无憾,我则见四野巉巉,不听的众口喃喃。明滴溜参儿相搀,剔团圞月儿初淡。柳色浓,桃花谢,红稀绿暗。想才郎常好是做得严,跳出这虎窟龙潭。
【四门子】要相逢怕甚牙儿占彡,呀,敢我紧妆着一半憨。过关津怕的是人虚站,又道我恰离家初二三。胆儿又虚,色儿又惨,百忙里蹿行马儿不住叫喊。脚儿又疾,口儿又喃,我见他头低眼目斩。
【古水仙子】将将将紫丝韁紧兜揽,是是是春纤长勒不住碧玉衔。飕飕飕摔风过长亭,出出出方行过短站。见见见三家店忽的向南,淹淹淹映香尘晓日红含。我我我软兀剌绣鞍身半探,看看看曲弯弯两叶蛾眉淡,瘦怯怯六幅翠裙搀。
【寨儿令】尴九咸,尴九咸,做的来所事忒严。想当初才貌两相堪,一个是娇仕女,一个俊儿男,他自把那婚姻勘。
【神仗儿】袄庙锁足乞塔的对岩,蓝桥上忽剌剌的水淹,将一对小小夫妻送的来他羞我惨。娇娇媚媚,甜甜也那绀绀,半路里被人坑陷,我我我则落的眼儿馋。
【尾声】一担相思自摇撼,我和你两家担由自难担,将一个担不起担儿却怎生分付俺。
 郝经
郝经 刘向 编
刘向 编 司马迁
司马迁 张养浩
张养浩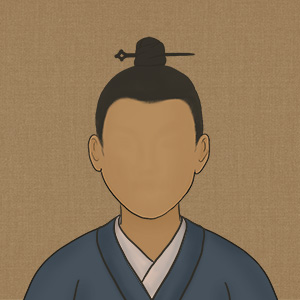 曾瑞
曾瑞 刘学箕
刘学箕 曹雪芹
曹雪芹 薛昭蕴
薛昭蕴 邓剡
邓剡 毛奇龄
毛奇龄 李清照
李清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