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浓绿的槐叶低向明窗室中有些发暗,艳红的石榴花盛开光彩耀眼明。美人邀我稍作停留不必远行。无奈行期已到烟雨迷漾中画船扬帆轻轻。
只见她柳眉伴着离歌紧皱,梨花面容有泪流倾。离别的情景确实不像初见时的欢乐之情。今夜月光明照的江上我在船中酒醉刚刚清醒。
注释
玉人:美人,指歌女。少,稍。
柳叶:指美女之眉,眉似柳叶,故称。
梨花:指美女面似梨花之娇美。
参考资料:
创作背景
这首词黄庭坚词作属别具一格之作。该词以柳叶和梨花来比喻伊人的双眉和脸庞,以“皱”眉和“倾”泪刻画伊人伤离的形象,通俗而又贴切。
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,原作者已无法考证。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,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赏析
该词写离别。上片写行客即将乘舟出发,正与伊人依依话别。作者先从写景人手,这时正当初夏,窗前槐树绿叶繁茂,所以室内显得昏暗,而室外榴花竞放,红艳似火,耀人双眼,这与室内气氛恰好形成强烈对比,两人此刻的心情没有明说,却以室内黯淡的气氛来曲折地反映。
离别在即,难舍难分,“玉人邀我少留行”,不仅是伊人在挽留,行客自己也是迟迟不愿离开。“无奈”两字一转,写出事与愿违,出发时间已到,不能迟留。接着绘出江上烟雨凄迷,轻舟挂帆待发,两人无限凄楚的别情就在这诗情画意的描述中宛转流露。
该词系双调,下片格式与上片相同。“柳叶”两句,承上片“无奈”而来,由于舟行在即,不能少留,而两人情意缠绵,难舍难分,真是“悲莫悲兮生别离”。“柳叶”两句,写临行饯别时伊人蹙眉而歌,泪如雨倾。这里运用比喻,以柳叶喻双眉,梨花喻脸庞。“别时”句又一转,由眼前凄凄惨惨的离别场面回想到当初相见时的欢乐情景,但往事不堪回首,只能使临行时的心情更加沉重。
末句略同柳永“今宵酒醒何处、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。词人悬想半夜酒醒,唯见月色皓洁,江水悠悠,无限离恨,尽在不言之中,如此写法颇具蕴藉含蓄之致。
参考资料:
黄庭坚(1045.8.9-1105.5.24),字鲁直,号山谷道人,晚号涪翁,洪州分宁(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)人,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,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,与杜甫、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“一祖三宗”(黄庭坚为其中一宗)之称。与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,合称为“苏门四学士”。生前与苏轼齐名,世称“苏黄”。著有《山谷词》,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,为“宋四家”之一。
管子曰:“仓廪实而知礼节。”民不足而可治者,自古及今,未之尝闻。古之人曰:“一夫不耕,或受之饥;一女不织,或受之寒。” 生之有时,而用之亡度,则物力必屈。古之治天下,至孅至悉也,,故其畜积足恃。今背本而趋末,食者甚众,是天下之大残也;淫侈之俗,日日以长,是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,莫之或止;大命将泛,莫之振救。生之者甚少,而靡之者甚多,天下财产何得不蹶!
汉之为汉,几四十年矣,公私之积,犹可哀痛!失时不雨,民且狼顾;岁恶不入,请卖爵子,既闻耳矣。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?世之有饥穰,天之行也,禹、汤被之矣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,国胡以相恤?卒然边境有急,数千百万之众,国胡以馈之?兵旱相乘,天下大屈,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;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。政治未毕通也,远方之能疑者,并举而争起矣。乃骇而图之,岂将有及乎?
夫积贮者,天下之大命也。苟粟多而财有余,何为而不成?以攻则取,以守则固,以战则胜。怀敌附远,何招而不至!今殴民而归之农,皆著于本;使天下各食其力,末技游食之民,转而缘南亩,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。可以为富安天下,而直为此廪廪也,窃为陛下惜之。
节自《汉书·食货志》
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。有业之,其色若自得者。听其言,约而尽。问之,王其姓。承福其名。世为京兆长安农夫。天宝之乱,发人为兵。持弓矢十叁年,有官勋,弃之来归。丧其土田,手衣食,馀叁十年。舍于市之主人,而归其屋食之当焉。视时屋食之贵贱,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;有馀,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。
又曰:“粟,稼而生者也;若布与帛。必蚕绩而后成者也;其他所以养生之具,皆待人力而后完也;吾皆赖之。然人不可遍为,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,理我所以生者也;而百官者,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,惟其所能,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,必有天殃,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。夫镘易能,可力焉,又诚有功;取其直虽劳无愧,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;心难强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于人,用心者使人,亦其宜也。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。
“嘻!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。有一至者焉,又往过之,则为墟矣;有再至、叁至者焉,而往过之,则为墟矣。问之其邻,或曰:“噫!刑戮也。”或曰:“身既死,而其子孙不能有也。”或曰:“死而归之官也。”吾以是观之,非所谓食焉怠其事,而得天殃者邪?非强心以智而不足,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?非多行可愧,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?将富贵难守,薄宝而厚飨之者邪?抑丰悴有时,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?吾之心悯焉,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乐富贵而悲贫贱,我岂异于人哉?”
又曰:“功大者,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与子,皆养于我者也;吾能薄而功小,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谓劳力者,若立吾家而力不足,则心又劳也。”一身而二任焉,虽圣者石可为也。
愈始闻而惑之,又从而思之,盖所谓“独善其身”者也。然吾有讥焉;谓其自为也过多,其为人也过少。其学杨朱之道者邪?杨之道,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,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,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?虽然,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,而患失之者,以济其生之欲,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,其亦远矣!又其言,有可以警余者,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。
凰枝。对景嗟咨,楚江风霜剪鸳鸯翅,渭城柳烟笼翡翠丝。缀黄金菊露,碎
绿锦荷花瑟瑟。
【梁州】叹落落情怀不已,恨匆匆岁月何之。拥并也似一片闲愁,撺掇出伤
心故事。往常时花笺写恨,红叶题诗,都做了风中飞絮,水上浮萍。痛煞煞玉连
环掂的瑕疵,碜可可锦回文揉的参差。瘦廉纤对妆奁金粉慵施,愁荏苒绣房中拈
针慵使,病恹渐锦筝ㄐ雁柱慵支。念兹,对此。匆匆岁月三之二,恰初三,早初
四。呖呖风前孤雁儿,感起我一弄儿嗟咨。
【黄钟尾声】雁儿,你写西风曲似苍颉字,对南浦愁如宋玉词。恰春归,早
秋至,多寒温,少传示。恼人肠,聒人耳,碎人心,堕人志。雁儿,直被你撺掇
出无限相思,偏怎生不寄俺有情分故人书半纸。
一千顷,都镜净,倒碧峰。忽然浪起,掀舞一叶白头翁。堪笑兰台公子,未解庄生天籁,刚道有雌雄。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。
春到兰湖少住,肯殷勤、访梅寻柳。相思人远,带围宽减,粉痕消瘦。双燕无凭,尺书难表,甚时回首。想画栏,倚遍东风,闲负却、桃花咒。
 黄庭坚
黄庭坚 李白
李白 贾谊
贾谊 司马迁
司马迁 韩愈
韩愈 关汉卿
关汉卿 贯云石
贯云石 苏轼
苏轼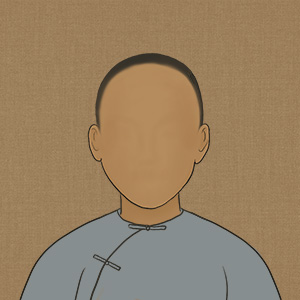 刘镇
刘镇 毛滂
毛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