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她穿着一身洁白如雪的衣服,就好像一枝美丽的梅花般好看。这位曳着雪白衣裙的女子,正含情脉脉,带着羞涩的微笑,姗姗来到我的梦中。
如果这位白衣女子来到越溪边,置身于一群身穿红色衣裙的越国美女中,那情景就好像一片红色的莲花中绽放了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。
注释
赠道者:一作“赠送”。道者:道士。
麻衣如雪:语出《诗经·曹风·蜉蝣》,此处借用来描绘女子一身如雪的白衣。
越溪:春秋末年越国美女西施浣纱的地方。末两句是诗人的想象。
参考资料:
赏析
此诗从题目“赠道者”可以看出,诗赠送的对象是个道士,从诗的内容看,这是个女道士。此诗题目一作“赠送”。如果是后一个题目,那么,他写赠的对象就不一定是个女道士。但无论用哪一个题目,都不难看出,诗人所要着意描绘的是一个漂亮的白衣女子,并且对她的美色是颇为倾倒的。
首句中的“麻衣如雪”,出于《国风·曹风·蜉蝣》,这里借用来描画女子所穿的一身雪白的衣裳。在形容了女子的衣着以后,诗人又以高雅素洁的白梅来比拟女子的体态、风韵。次句中的“微妆”,是“凝妆”、“浓妆”的反义词,与常用的“素妆”、“淡妆”意义相近。“笑掩”写女子那带有羞涩的微笑。这女子是如此动人,她曳着雪白的衣裙,含情脉脉地微笑着,正姗姗来到诗人的梦境。
从甜蜜的梦境中醒来,诗人不禁浮想联翩,以致在他眼前呈现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美丽境界:他仿佛看到这一女子来到越国的一条溪水边,走进一群穿着红色衣裳的浣纱女子中间;那风姿,那神韵,是这般炫人眼目,就像是开放在一片红色荷花中的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。这两句,以“若”字领起,说明这是诗人的假想之词。首两句说的是女子的神,此两句则是说女子的形,然而在写法上却不似前两句作直接的描绘,而以烘托之法让人去想象和思索。当女子置身于漂亮的越女中间时,她便像是红莲池中开放的一朵玉洁冰清的白莲;她的婀娜娇美,自然不言而喻了。
在表现手法上,此诗主要采用了拟物的手法。一处用“一枝梅”,一处用“白莲”,后者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当然,以莲花比美人,并不是武元衡的独创。稍晚于武元衡的白居易也曾以莲花比女子,如“姑山半峰看,瑶水一枝莲(《玉真张观主下小女冠阿容》)。但比较地说,白居易只是运用了拟物一种手法,以形象显出单纯的美;武元衡在拟物时,兼用了烘托的手法,让诗中女子在一群越女的映衬下亮相,然后再过渡到莲花的比拟上,更有一种优美的意境和特殊的艺术效果。不过,全诗的情调只是在吐露对白衣少女美貌的神往之情,诗旨便不可取了。
参考资料:
武元衡(758―815),唐代诗人、政治家,字伯苍。缑氏(今河南偃师东南)人。武则天曾侄孙。建中四年,登进士第,累辟使府,至监察御史,后改华原县令。德宗知其才,召授比部员外郎。岁内,三迁至右司郎中,寻擢御史中丞。顺宗立,罢为右庶子。宪宗即位,复前官,进户部侍郎。元和二年,拜门下侍郎平章事,寻出为剑南节度使。元和八年,征还秉政,早朝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遣刺客刺死。赠司徒,谥忠愍。《临淮集》十卷,今编诗二卷。
山木多蓊郁,兹桐独亭亭。叶重碧云片,花簇紫霞英。
是时三月天,春暖山雨晴。夜色向月浅,闇香随风轻。
行者多商贾,居者悉黎氓。无人解赏爱,有客独屏营。
手攀花枝立,足蹋花影行。生怜不得所,死欲扬其声。
截为天子琴,刻作古人形。云待我成器,荐之于穆清。
诚是君子心,恐非草木情。胡为爱其华,而反伤其生。
老龟被刳肠,不如无神灵。雄鸡自断尾,不愿为牺牲。
况此好颜色,花紫叶青青。宜遂天地性,忍加刀斧刑。
我思五丁力,拔入九重城。当君正殿栽,花叶生光晶。
上对月中桂,下覆阶前蓂。汎拂香炉烟,隐映斧藻屏。
为君布绿阴,当暑荫轩楹。沈沈绿满地,桃李不敢争。
为君发清韵,风来如叩琼。泠泠声满耳,郑卫不足听。
受君封植力,不独吐芬馨。助君行春令,开花应晴明。
受君雨露恩,不独含芳荣。戒君无戏言,剪叶封弟兄。
受君岁月功,不独资生成。为君长高枝,凤皇上头鸣。
一鸣君万岁,寿如山不倾。再鸣万人泰,泰阶为之平。
如何有此用,幽滞在岩坰。岁月不尔驻,孤芳坐凋零。
请向桐枝上,为余题姓名。待余有势力,移尔献丹庭。
一闭上阳多少春。玄宗末岁初选入,入时十六今六十。
同时采择百馀人,零落年深残此身。忆昔吞悲别亲族,
扶入车中不教哭。皆云入内便承恩,脸似芙蓉胸似玉。
未容君王得见面,已被杨妃遥侧目。妒令潜配上阳宫,
一生遂向空房宿。宿空房,秋夜长,夜长无寐天不明。
耿耿残灯背壁影,萧萧暗雨打窗声。春日迟,
日迟独坐天难暮。宫莺百啭愁厌闻,梁燕双栖老休妒。
莺归燕去长悄然,春往秋来不记年。唯向深宫望明月,
东西四五百回圆。今日宫中年最老,大家遥赐尚书号。
小头鞋履窄衣裳,青黛点眉眉细长。外人不见见应笑,
天宝末年时世妆。上阳人,苦最多。少亦苦,老亦苦,
少苦老苦两如何。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,
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。
有冯虚公子者,心侈体忲,雅好博古,学乎旧史氏,是以多识前代之载。言于安处先生曰:夫人在阳时则舒,在阴时则惨,此牵乎天者也。处沃土则逸,处瘠土则劳,此系乎地者也。惨则鲜于欢,劳则褊于惠,能违之者寡矣。小必有之,大亦宜然。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,兆人承上教以成俗,化俗之本,有与推移,何以核诸?秦据雍而强,周即豫而弱,高祖都西而泰,光武处东而约,政之兴衰,恒由此作。先生独不见西京之事欤?请为吾子陈之。
汉氏初都,在渭之涘,秦里其朔,实为咸阳。左有崤函重险、桃林之塞,缀以二华,巨灵赑屃,高掌远跖,以流河曲,厥迹犹存。右有陇坻之隘,隔阂华戎,岐梁汧雍,陈宝鸣鸡在焉。于前终南太一,隆崛崔萃,隐辚郁律,连冈乎嶓冢,抱杜含户,欱沣吐镐,爰有蓝田珍玉,是之自出。于后则高陵平原,据渭踞泾,澶漫靡迤,作镇于近。其远则九嵕甘泉,涸阴冱寒,日北至而含冻,此焉清暑。尔乃广衍沃野,厥田上上,实为地之奥区神皋。昔者,大帝说秦穆公而觐之,飨以钧天广乐。帝有醉焉,乃为金策,锡用此土,而翦诸鹑首。是时也,并为强国者有六,然而四海同宅西秦,岂不诡哉!
自我高祖之始入也,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。娄敬委辂,斡非其议,天启其心,人惎之谋,及帝图时,意亦有虑乎神祇,宜其可定以为天邑。岂伊不虔思于天衢?岂伊不怀归于枌榆?天命不滔,畴敢以渝!
于是量径轮,考广袤,经城洫,营郭郛,取殊裁于八都,岂启度于往旧。乃览秦制,跨周法,狭百堵之侧陋,增九筵之迫胁。正紫宫于未央,表峣阙于闻阖。疏龙首以抗殿,状巍峨以岌嶪。亘雄虹之长梁,结棼橑以相接。蔕倒茄于藻井,披红葩之狎猎。饰华榱与璧珰,流景曜之韡晔。雕楹玉磶,绣栭云楣。三阶重轩,镂槛文?。右平左域,青琐丹墀。刊层平堂,设切厓隒。坻崿鳞眴,栈齴巉嶮。襄岸夷涂,修路陵险。重门袭固,奸宄是防。仰福帝居,阳曜阴藏。洪钟万钧,猛虡趪趪。负笋业而余怒,乃奋翅而腾骤。
朝堂承东,温调延北,西有玉台,联以昆德。嵯峨崨嶪,罔识所则。若夫长年神仙,宣室玉堂,麒麟朱鸟,龙兴含章,譬众星之环极,叛赫戏以辉煌。正殿路寝,用朝群辟。大夏耽耽,九户开辟。嘉木树庭,芳草如积。高门有闶,列坐金狄,内有常侍谒者,奉命当御。兰台金马,递宿迭居。次有天禄石渠校文之处,重以虎威章沟严更之署。徼道外周,千庐内附,卫尉八屯,警夜巡昼。植铩悬犬,用戒不虞。
后宫则昭阳飞翔,增成合欢,兰林披香,凤凰鸳鸾。群窈窕之华丽,嗟内顾之所观。故其馆室次舍,采饰纤缛。裛以藻绣,文以朱绿,翡翠火齐,络以美玉。流悬黎之夜光,缀随珠以为烛。金戺玉阶,彤庭辉辉。珊瑚林碧,瓀珉磷彬。珍物罗生,焕若昆仑。虽厥裁之不广,侈靡逾乎至尊。于是钩陈之外,阁道穹隆,属长乐与明光,径北通乎桂宫。命般尔之巧匠,尽变态乎其中。后宫不移,乐不徙悬,门卫供帐,官以物辨。恣意所幸,下辇成燕。穷年忘归,犹弗能遍。瑰异日新,殚所未见。
惟帝王之神丽,惧尊卑之不殊。虽斯宇之既坦,心犹凭而未摅 ,思比象于紫微,恨阿房之不可庐。覛往昔之遗馆。获林光于秦余。处甘泉之爽垲,乃隆崇而弘敷。既新作于迎风,增露寒与储胥。托乔基于山冈,直滞霓以高居。通天訬以竦峙,径百常而茎擢。上辩华以交纷,下刻哨其若削,翔鹤仰而不逮,况青鸟与簧雀。伏棂槛而俯听,闻雷霆之相激。
柏梁既灾,越巫陈方。建章是经,用厌火祥。营宇之制,事兼未央。圜阙竦以造天,若双碣之相望。凤骞翥于甍标,咸溯风甫欲翔。阊阖之内,别风嶕峣。何工巧之瑰玮,交绮豁以疏寮。干云雾而上达,状亭亭以苕苕。神明崛其特起,井干叠而百增。跱游极于浮柱,结重栾以相承。累层构而遂隮,望北辰而高兴。消氛埃于中宸,集重阳之清澄。瞰宛虹之长鬐,察云师之所凭。上飞闼而仰眺,正睹瑶光与玉绳。将乍往而未半,休悼栗而怂兢,非都卢之轻趫,孰能超而究升?
驭娑骀荡?焘弄桔桀。枍诣承光,睽瓜庨豁。增桴重棼,锷锷列列。反宇业业,飞檐??。流景内照,引曜日月。天梁之宫,实开高闱。旗不脱扃,结驷方蕲。轹辐轻骛,容于一扉。长廊广庑.途阁云蔓。闬庭诡异,门千户万。重闺幽闼,转相逾延。望?窱以径延,眇不知其所返。既乃珍台蹇产以极壮,橙道逦倚以正东。似阆风之遐扳,横西洫而绝金墉。城尉不弛拆,而内外潜通。
前开唐中,弥望广橡。顾临太液,沧池漭沆。渐台立子中央;赫昈昈以弘敞。清渊洋洋,神山峨峨。列瀛洲与方丈,夹蓬莱而骈罗。上林岑以垒嶵,下崭严以岩龉。长风激于别岛,起洪涛而扬波。浸石菌于重涯,濯灵芝以朱柯。海若游于玄渚,鲸宜失流而蹉跎。于是采少君之端信,庶栾大之贞固。立修茎之仙掌,承云表之清露。屑琼蕊以朝飧,必性命之可度。美往普之松乔,要羡门乎天路。想升龙于鼎湖,岂时俗之足慕。若历世而长存,何遽营乎陵墓!徒观其城郭之制,则旁开三门,参涂夷庭,方轨十二,街衢相经。廛里端直,甍宇齐平。北阙甲第,当道直启。程巧致功,期不纮陊。木衣绨锦,士被朱紫。武库禁兵,设在兰锜。匪石匪董,畴能宅此?尔乃廓开九市,通阛带阓。旗亭五重,俯察百隧。周制大胥,今也惟尉。瓌货方至,鸟集鳞萃。鬻者兼赢,求者不匮。尔乃商贾百族,裨贩夫妇,鬻良杂普,蚩眩边鄙。何必昏于作劳,邪赢优而足恃。彼肆人之男女,丽美奢乎许史。若夫翁伯浊质,张里之家,击钟鼎食,连骑相过。东京公侯,壮何能加?都邑游侠,张赵之伦,齐志无忌,拟迹田文。轻死重气,结党连群?实蕃有徒,其从如云。茂陵之原,阳陵之朱。趫悍虓豁,如虎如貙。睚眦虿芥,尸僵路隅。丞相欲以赎子罪,阳石污而公孙诛。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,街谈巷议,弹射臧否,剖析毫厘,擘肌分理。所好生毛羽,所恶成创痏。郊甸之内,乡邑殷赈。五都货殖,既迁既引。商旅联槅,隐隐展展。冠带交错,方辕接轸。封几千里,统以京尹。郡国宫馆,百四十五。右机盩屋,并卷酆鄠。左暨河华,遂至虢土。上林禁苑,跨谷弥阜。东至鼎湖,邪界细柳。掩长杨而联五柞,绕黄山而款牛首。缭垣绵联,四百余里。植物斯生,动物斯止。众鸟翩翻,群兽飚呆。散似惊波,聚以京峙,伯益不能名,隶首不能纪。林麓之饶,于何不有?木则枞括根楠,梓械楩枫。嘉卉灌丛,蔚若邓林。郁蓊薆薱,橚爽櫹椮。吐葩飓荣,布叶垂阴。草则箴莎营蒯,薇蕨荔苀,王蒭莔台,戎葵怀羊。苯莼蓬茸,弥皋被冈。筱荡敷衍,编町成篁。山谷原湿,泱漭无疆。乃有昆明灵沼,黑水玄址。周以金堤,树以柳杞。豫章珍馆,揭焉中峙。牵牛立其左,织女处其右,日月于是乎出入?象扶桑与檬汜。其中则有鼋鼍巨鳖,鳣鲤鱮鲖,鲔鲵鲿鲨,修额短项,大日折鼻,诡类殊种。鸟则鹔鹴鸹鸨,鴐鹅鸿鹤。上春候来?季秋就温。南翔衡阳,北栖雁门。奋隼归凫,沸卉軿訇。众形殊声,不可胜论。于是孟冬作阴,寒风肃杀。雨雪飘飘,冰霜惨烈。百卉具零,刚虫搏击。尔乃振天维,衍地络,荡川滨,簸林薄。鸟毕骇,兽咸作,草伏木栖,寓居穴托。起彼集此,霍绎纷泊,在彼灵囿之中,前后无有垠锷,虞人掌焉,为之营域。焚莱平场,柞木剪棘。结置百里,迒杜蹊塞。麀鹿虞虞,骈田逼仄。天子乃驾雕轸,六骏驳。戴翠帽,倚金较。璇弁玉缨?遗光倏爚。建玄弋,树招摇。栖鸣鸢,曳云梢。弧旌枉矢,虹旃蜕旄。华盖承辰,天毕前驱。千乘雷动,万骑龙趋。属车之篷,载猃猲獢。匪唯玩好,乃有秘书。小说九百,本自虞初。从容之求,实侯实储。于是蚩尤秉钺,奋鬣被般。禁御不若,以知神奸,魑魅魍魉,莫能逢旃。陈虎旅于飞廉,正垒壁乎上兰。结部曲,整行伍。燎京薪,骇雷鼓。纵猎徒,赴长莽。迾卒清候,武士赫怒。缇衣韎韐,睢盱拔扈。光炎烛天庭,嚣声震海浦。河渭为之波荡,吴狱为之陁堵。百禽棱遽,骙瞿奔触。丧精亡魂,失归忘趋。投轮关辐,不邀自遇。飞罕潚箾,流镝???。矢不虚舍,铤不苟跃。当足见蹍,值轮被轹。僵禽毙兽,烂若碛砾。但观置罗之所罥结,竿殳之所揘毕,叉簇之所搀捔,徒搏之所撞?,白日未及移其晷,巳狝其十七八。若夫游鷮高翚,绝坑逾斥。巉兔联猭,陵峦超壑。比诸东郭,莫之能获。乃有迅羽轻足,寻景追括。鸟不暇举,兽不碍发。青骹击于韝下,韩卢噬于緤末。及其猛毅髬髵,隅目高匡,威慑兕虎,莫之敢伉。乃使中黄之士,育获之俦,朱鬕髠髽,植发如竿。袒裼戟手,奎踽盘桓。鼻赤象,圈巨狿,摣狒猬,?窳狻,揩枳落,突棘藩。梗林为之靡拉,朴丛为之摧残。轻锐僄狡,趫捷之徒,赴洞穴,探封狐。陵重巘,猎昆駼。杪木末,攫獑猢。超殊榛,摕飞鼯。是时,后宫嬖人昭仪之伦,常亚子乘舆。慕贾氏之如皋,《北风》之同车。盘于游畋,其乐只且。于是鸟兽殚,目观穷。迁延邪睨,集乎长杨之宫。息行夫,展车马。收禽举胔,数课众寡。置互摆牲,颁赐获卤。割鲜野飨;镐勤赏功。五军六师,千列盲重。酒车酌醴,方驾授饔。升觞举燧,既釂鸣钟。膳夫驰骑,察贰廉空。炙炮伙,清酤?。皇恩溥怖,洪德施。'徒御悦,士忘罢。巾车命驾?回旆右移。相羊乎五柞之馆,旋憩乎昆明之池。登豫章,简矰红。蒲且发,弋高鸿。挂白鹊,联飞龙。磻不待絓,往必加双。于是命舟牧,为水嬉。浮鷁首,翳云芝。垂翟葆,建羽旗。齐枻女,纵悼歌。发引和,校鸣葭。奏《淮南》,度《阳阿》。感河冯,怀湘娥。惊蛔蛹,惮蚊蛇。然后钓鲂鳢,缅鰋鲉。摭紫贝,搏耆龟。捞水豹旱潜牛。泽虞是滥,何有春秋?擿漻澥,搜川渎。布九罭,设罣蔍。摧昆鲕,殄水族。蓬藕拔,蜃蛤剥。逞欲畋斁,效获麑麃。谬蓼浡浪,乾池涤薮。上无逸飞,下无遗走。攫胎拾卵,纸缘尽取。取乐今日,遑恤我后!
既定且宁,焉知倾陁?大驾幸乎平乐,张甲乙而袭翠被。攒珍宝之玩好,纷瑰丽以侈靡。临迥望之广场,程角抵之妙戏。乌获扛鼎,都卢寻撞。冲狭燕濯,胸突铦锋。跳丸剑之挥霍,走索上而相逢。华岳峨峨,冈峦参差。神木灵草,朱实离离.总会仙倡,戏豹舞罴。白虎鼓瑟,苍龙吹篪。女娥坐而长歌,声清畅而蜲蛇.洪涯立而指麾,被毛羽之襳襹。度曲未终,云起雪飞。初若飘飘,后遂霏霏。复陆重阁,转石成雷。礔砺激而增响,磅盖象乎天威。巨兽百寻,是为曼延。神山崔巍,欻从背见。熊虎升而挐攫,猿狖超而高援。怪兽陆梁,大雀踆踆。白象行孕,垂鼻磷囷。海鳞变而成龙,状婉婉以昷昷。舍利飏飏,化为仙车,骊驾四鹿,芝盖九葩。蟾蜍与龟,水人弄蛇。奇幻倏忽,易貌分形。吞刀吐火,云雾杏冥。画地成川,流渭通泾。东海黄公,赤刀粤祝。冀厌白虎,卒不能救。挟邪作蛊,于是不售。尔乃建戏车,树修旃。伥僮程材,上下翩翻。突倒投而跟絓,譬陨绝而复联。百马同辔,骋足并驰。撞末之技,态不可弥。弯弓射乎西羌,又顾发乎鲜卑。
于是众变尽,心酲醉。般乐极,怅怀萃。阴戒期门,微行要屈。降尊就卑,怀玺藏绂。便旋闾阎,周观郊遂。若神龙之变化,章后皇之为贵。然后历掖庭,适欢馆。捐衰色,从嬿婉。促中堂之狭坐,羽觞行而无算。秘舞更奏,妙材骋技。妖蛊艳夫夏姬,美声畅于虞氏。始徐进而嬴形,似不任乎罗绮。嚼清商而却转、增婵娟以此豸。纷纵体而迅赴,若惊鹤之群罢。振朱屣于盘樽,奋长袖之飒俪。要绍修态,丽服飏菁。眠藐流眄,一顾倾城。展季桑门,谁能不营?列爵十四,竟媚取荣。盛衰无常,唯爱所丁。卫后兴于鬓发,飞燕宠于体轻。尔乃逞志究欲,穷身极娱。鉴戒《唐诗》,他人是偷。自君作故,何礼之拘?增昭仪于婕妤,贤既公而又侯。许赵氏以无上,思致董于有虞。王闳争坐于侧,汉载安而不渝。
高祖创业,继体承基。暂劳永逸,无为而治。耽乐是从,何虑何思?多历年所,二百余期。徒以地沃野丰,百物殷阜;岩险周固,衿带易守。得之者强,据之者久。流长则难竭,柢深则难朽。故奢泰肆情,馨烈弥茂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,传闻于未闻之者,曾仿佛其若梦,未一隅之能睹。此何与于殷人之屡迁,前八而后五,居相圮耿,不常厥土。盘庚作诰,帅人以苦。方今圣上,同天号于帝皇,掩四海而为家。富有之业,莫我大也。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,独俭啬以龌龊。忘《蟋蟀》之谓何?岂欲之而不能,将能之而不欲欤?蒙窃惑焉,愿闻所以辩之之说也。
远水晴天明落霞,古岸渔村横钓槎。翠帘沽酒家,画桥吹柳花。
二客同游过虎溪,一径无尘穿翠微。寸心流水知,小窗明月归。
春夜
灯下愁春愁未醒,枕上吟诗吟未成。杏花残月明,竹根流水声。
春思三首
莺羽金衣舒晚风,燕嘴香泥沾乱红。翠帘花影重,五人春睡浓。
春柳长亭倾酒樽,秋菊东篱洒泪痕。思君不见君,倚门空闭门。
帘外轻寒归燕忙,桥下残红流水香。游人窥粉墙,玉骢嘶绿杨。
回首赤壁矶边,骑鲸人去,几度山花发。澹澹长空今古梦,只有归鸿明灭。我欲从公,乘风归去,散此麒麟发。三山安在,玉箫吹断明月!
 武元衡
武元衡 白居易
白居易 张衡
张衡 张可久
张可久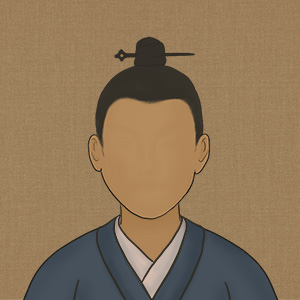 仇远
仇远 李珣
李珣 王国维
王国维 陈亮
陈亮 赵秉文
赵秉文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